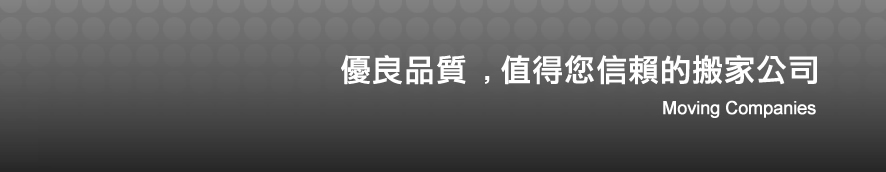文章来源:由「百度新聞」平台非商業用途取用"http://www.lifeweek.com.cn/2006/0627/15689.shtml"
《西藏日報》第一任攝影記者陳宗烈先生告訴記者,上世紀50年代后半期,他經常騎馬乘船,帶著幾天的糌粑和酥油,游歷西藏各地的莊園和寺廟。50年代的西藏還沒有土改,相當于內地秦漢時期的奴隸——封建莊園制還普遍存在。陳宗烈說,當時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年楚河兩岸莊園遍地。而今天,記者駕車沿雅魯藏布江、拉薩河和年楚河兩岸行走,遍地村莊,似乎難辨與當年的區別。尤其在山南和年楚河兩岸,田園和村落的富庶比山北更勝一籌。十世德木活佛的兒子旺久多吉先生說,過去一個大貴族或者寺院擁有的莊園通常可以達到上百甚至幾百個,有些范圍甚至遍及全藏。旺久多吉的父親,十世德木活佛德木寺的莊園就從拉薩東部的林芝一直延續到接近西藏的八宿。記者的眾多采訪對象,或是舊西藏大貴族的后代,曾在莊園中度過自己的無憂童年;或曾在貴族莊園中借居生活、工作,親眼見證了西藏貴族生活的最后余暉。這些貴族莊園曾無比繁華和奢侈,如果它們依然存在,也許如法國羅納河兩岸數百座古堡一樣,將成為極具價值的歷史活體。然而遺憾的是,上世紀50年代還曾存在的數千座大小貴族莊園,在半個世紀甚至更短的時間內迅速煙消云散了,絕大部分甚至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記者的采訪對象,比如陳宗烈先生等,曾目睹了諸如甲瑪池康、拉加里和朗色林等莊園最后的時刻。而這些曾馳名全藏的莊園,如今除了殘存的遺跡,只是在陳先生等人的攝影鏡頭下留下了最后的影像。聽說記者想去尋訪最后的貴族莊園,西藏文化廳前副廳長甲央勸說不要抱太大希望。甲央說,目前全西藏唯一保存完整的只有位于江孜的帕拉莊園。其余莊園,比如阿沛·阿旺晉美出生的甲瑪池康已經全毀于改道的洪水,其余的絕大多數已經在“文革”中被拆除。許多過去著名的貴族莊園由于消失時間太久,消失得過于徹底,甚至今天連自治區文物局宣保處處長格桑頓珠都沒有聽說過。格桑頓珠說,除了帕拉莊園,曾經顯赫的朗色林莊園和拉加里莊園都只剩下遺址。“在那里你基本上看不到太多,剩下的一點建筑也快要崩塌了。”格桑頓珠說,“我們準備對拉加里和朗色林莊園進行整修,但工程還沒有全面開始。”驅車從唐古拉山口到那曲,從拉薩到日喀則和江孜,沿途藏族人的田園生活讓人以為他們千百年來就如此甜美,并亙古不變地延續至今。然而整個西藏和這里的人民卻經歷了本世紀人類最劇烈和復雜的劇變。從那曲出來經羅馬鎮,這里曾經是羅馬日瓦部落的領地。1956年初冬,陳宗烈前往那曲記者站時曾來到過這里,他曾在這里遇到一個當地牧民頓珠,頓珠的出生地就是“羅馬日瓦”,不諳國事和世事。當時對于這些部落百姓來說,生活就是給大小頭人上貢,交付酥油、實物或者現金,只知道自己是誰的屬民。在舊貴族階層和莊園同樣消失的今日西藏,問及過去歷史,人們的記憶已經和湮滅的莊園一樣逐漸模糊。采訪對象們,有的當年親眼所見莊園內的殘忍和無情,有的卻充滿感情地回憶某些開明貴族的仁慈。發現并描繪西藏貴族和莊園最后一抹余暉落下,并非記者在短暫時間所能完成的任務,但對于未來前往西藏旅行的你,也許能在某個過去的莊園發現一些值得回味的秘密。帕拉莊園——一個貴族家庭的縮影當汽車從雄渾的雅魯藏布江峽谷中駛出接近日喀則時,近乎沙漠化的雅魯藏布江兩岸綠色逐漸多起來。在藏語中日喀則意為“最好的莊園”,傳統上屬班禪的勢力范圍。遠處扎什倫布寺的金頂在正午耀眼的陽光下閃閃發光。陳宗烈說,他上世紀50年代第一次到達日喀則時曾覺得這里景色荒蕪,頗為失望。但隨著道路折向西南,繼續向白朗和江孜方向行駛時,公路兩邊的田地顯得愈加開闊,日漸密集的村落僅從房屋大小和裝飾來看,也遠比日喀則附近顯得富足。當遠遠路左看見白居寺山上的紅色圍墻和江孜宗山城堡時,馬路右側出現了帕拉莊園的石碑。這里是江孜江熱鄉的班久倫布村。西藏唯一保存完整的帕拉莊園就在這里。從帕拉莊園側門進去,記者找到了莊園負責人白多。這是個身材矮小的藏族老頭,從莊園三樓下來的時候背著一個老式舊黃挎包。聽說記者試圖尋找莊園后人的來意,他顯得有些不太情愿。來西藏前,從沒有想到尋找舊貴族和他們后人是這樣看似容易卻非常困難。從西藏自治區統戰部前部長頓珠多吉先生、西藏政協前副主席徐洪森先生和自治區黨委宣傳部新聞出版處莊勁松處長那里本來獲得很多過去西藏上層人士的信息,但在實際聯絡中卻一無所獲。白多操著不太熟練的漢語說:“我要接待參觀,不能離開。我不在,領導會批評,他們批評很厲害!”6月18日上午9點,大門緊閉的帕拉莊園內沒有一個游人。站在莊園主樓右側搖搖欲墜的木制樓梯上,記者再三勸說白多幫助引見帕拉家的后人,昨天他已經告訴我們,帕拉家的后人就在江孜,據說是一位縣政協委員。走走停停的白多最終把我們引到距莊園大門只有幾十米的一個院子前,如果準確形容,這個院子比莊園附近其他漂亮的民居更顯寒酸些。門前兩邊的墻上整整齊齊貼滿牛糞,牛糞上所有手指印都朝一個方向,遠看好像是刻意的裝飾。牛糞是藏人心目中的寶貝,但是出現在一個貴族后裔的院墻上,總有奇怪的感覺。敲開大門,院里是幾頭安靜吃草的牛,一條突然狂吠的大黑狗把隨同前來的導游姑娘徐陽嚇得不敢進門。這是一棟普通的兩層藏式小樓,泥夯的外墻已經有點陳舊,木制門框上釘著的鐵牌上寫著“優秀養牛戶”的字樣。帕拉家族的后人之一羅布次仁就站在院子里,一臉憨厚的笑容。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羅布次仁與記者在照片上見過的舊貴族形象仍大相徑庭。他身材中等,面色紅黑,戴著一頂藏族人常見的舊氈帽,笑容滿面,非常熱情。沿狹窄搖晃的木梯上了二樓天井平臺,羅布次仁的妻子端上甜茶。白多讓我們看墻上的一個說明牌,這個類似旅游景點的說明牌上是對羅布次仁的簡介。雖然是江孜縣政協委員,但羅布次仁夫婦都不懂漢語,似乎這個用漢語寫就的牌子能簡化許多人的好奇心。白多此時似乎忘記了他的工作,連莊園年輕的導游格桑也來幫助翻譯。出乎意料的是,羅布次仁的父親雖然正是大貴族帕拉三兄弟中的老二扎西旺久,也是帕拉莊園的莊主,但他本人卻從來都不是貴族。有高貴血統、又有著淵源歷史的帕拉家族正是舊西藏僅有的5個第本家族之一。記者曾請教過中國臧學研究中心的次仁央宗女士,她說帕拉家族最顯赫的經歷是曾經出現過5個噶倫,家族的宅邸原來位于拉薩大昭寺附近八廓東街,而家族的莊園在全西藏超過上百處。羅布次仁的父親是帕拉家族曾擔任江孜宗本的帕拉·平措朗杰和大貴族夏扎家的女兒生的三個兒子之一。作為家長的平措朗杰的長子,土登沃丹曾經是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僧官。為了延續帕拉家族的血脈,但又不想因為兄弟分家而讓家族財產分割,從源于第五世達賴喇嘛的貴族“貢桑孜”家族娶回了一個女子。然而羅布次仁的父親帕拉·扎西旺久并不愿意與兄弟共同擁有一個妻子。次仁央宗說,為了安撫他,大哥土登沃丹就把帕拉·扎西旺久從拉薩送到家族在江孜的帕拉莊園。羅布次仁說,他的父親正是在這里遇到了母親拉珍。白多告訴我,帕拉家族原來的主莊園在江孜的江嘎村,1904年榮赫鵬率英國侵略軍入侵江孜時,江嘎的主莊園全部被英國人焚毀。在莊園的陽臺上就可以看見宗山的城堡,那里真是當年抗英的戰場。上世紀30年代,扎西旺久從拉薩回到江孜,才在藏歷火牛年(1937年)將主莊園從江嘎遷到班久倫布村。羅布次仁的母親拉珍祖上便是從江嘎村搬來的農奴,拉珍本人是帕拉莊園的釀酒師。羅布次仁說,在父親來到帕拉莊園之前,母親曾和莊園的管家朗杰生了一個孩子。當帕拉·扎西旺久來到帕拉莊園后,他把前管家朗杰支到另一個莊園,并與拉珍開始了一種更輕松的生活。羅布次仁和他的姐姐、弟弟就是這段生活的結晶。次仁央宗說,在貴族社會,這種情形并不少見。貴族和農奴——難以逾越的鴻溝莊園建筑依然讓人回憶起這段似乎浪漫的故事。走進帕拉莊園的木質大門,迎面大天井右邊的兩層樓上就是拉珍當年的釀酒作坊,當年釀酒的灶臺上已經蒙滿了灰塵。羅布次仁說,小時候他就和母親住在這里,自從1959年離開帕拉莊園后,羅布次仁直到80年代才第一次重新走進離家咫尺之遙的莊園大門。略顯陰暗的房間里,留下的只有灶臺和釀酒用的陶罐,這是羅布次仁再熟悉不過的了。他似乎在尋找什麼,拍著房間的墻壁告訴記者,這里本來有個門,通往隔壁的房間。父親扎西旺久的臥室在天井對面的三層樓上,幼年的羅布次仁能隨意前往莊園的任意一個房間,但母親和父親居室的高低還是顯示出他們之間不可逾越的等級——莊園主夫人的房間就在男主人的隔壁。西藏貴族社會的等級森嚴雖然能容忍貴族的風流韻事,但現實的婚姻卻永遠是貴族間鞏固利益和地位的工具,它絕不可能出現在羅布次仁的父親帕拉·扎西旺久和一個釀酒女之間。此前帕拉·多杰旺久和哥哥扎西旺久共娶了妻子并生了8個孩子,后來又和拉珍生了羅布次仁等3個孩子,但是和拉珍的關系是無法獲得貴族階層認可的。羅布次仁說,7歲那年,他的父親扎西旺久迎娶了江孜卓薩家的女兒做夫人,而讓拉珍和新的男管家丹達結了婚。夫人的臥室至今仍能看出當年西藏貴族婦女的奢華:描金的柜子上貼著上海30年代的招貼畫,有的柜子上描繪著內地式樣的繪畫。有杜十娘怒沉百寶箱、蘇小妹三難秦少游、女秀才移花接木、喬太守亂點鴛鴦譜……漢地和藏地、清代和民國的風格同時出現在這里,當然少不了銅鍍金的佛龕。在它旁邊的梳妝臺上,各種外國進口的化妝品和香水一應俱全。羅布次仁和母親生活的變化則似乎并不多,因為父親為他們母子在莊園外修了新的房子,羅布次仁和兄弟姐姐還能過過去的生活。另一個永遠不會改變的事實就是,他們永遠不能享有貴族子女的身份,即便他是帕拉貴族的血脈。農奴和貴族間的鴻溝在當時的西藏,比雅魯藏布江還要難以逾越。我和羅布次仁一家留了一張合影。卓拉抱著小孫子,這是非常和睦而幸福的一家。復雜的歷史和家庭背景今天看來并沒有給他們帶來什麼陰影和拖累。羅布次仁說,他們和過去莊園的農奴相處得很好,現在的房子就是村民幫助蓋的。白多讓我們看羅布次仁家的臥室墻上的兩個大相框,那里是羅布次仁的父親和伯父等親屬從國外寄來的照片。從照片上看,羅布次仁與他的父親、帕拉莊園的前主人帕拉·扎西旺久非常相像。帕拉·扎西旺久去了印度,直到1984年去世前的幾年,才和羅布次仁兄弟有了通信聯系,而母親拉珍是1993年去世的。六世達賴喇嘛雖然愛戀著瑪吉阿米,但以他的高貴也免不了被罷黜的代價。貴族和奴隸的愛情雖然可能萌發一時,但誰都能猜到最終的結局。我曾經詢問陳宗烈先生,貴族和奴隸之間到底隔著多深的鴻溝?他用自己在西藏的生活經歷和見聞給我做了具體解釋:“當時《西藏日報》曾吸納了許多進步貴族,比如報社副總編輯、出身于日喀則貴族家庭的擦珠·阿旺洛桑活佛;《西藏日報》社藏文編輯部顧問、出身于西藏郡王頗羅鼐家族的江樂金公爵。江樂金曾經是舊藏政府的四品官,很有地位。我借用他的牌子跟他到處走,通行無阻。”陳宗烈說,貴族身份的光環即便在解放后也并未褪色,農奴階層對貴族的敬畏,事實上在西藏解放后多年也難以消除。“我們報社還有一些職工出身農奴,他們見到貴族還是改不了吐舌頭、彎腰、落辮的習慣。比如江樂金,所有藏族職工見到他,都躬腰站在路邊,畢恭畢敬稱呼他‘公爵大人,您貴體安康!’”貴族的生活——奢華和現代的交織50年代的紀律不允許漢族干部隨便去藏族人家做客,尤其是貴族。作為舊貴族的《西藏日報》副主編曾幾次請陳宗烈去做客,但陳宗烈最終只能推托有事不去。“他也能看出來,也覺得遺憾,當然他也知道我的難處。實際上,當時我是很想去看看他們是怎樣生活的。”但陳宗烈終于有機會前往大貴族也布希·朗頓家。這位曾擔任過西藏政協副主席的大貴族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親侄子,還當過舊藏政府的噶倫和司倫。朗頓的家正好在當時西藏軍區大院旁邊,西藏軍區政治部本來就是他們家大宅院的一部分。在和平解放后土改前,朗頓就把院子讓出來給了軍區,于是從軍區大院進朗頓家的大院變得非常方便。陳宗烈說,朗頓是一個愛國的上層貴族,意識里根深蒂固的概念就是西藏屬于中國,西藏必須服從中央政府。陳宗烈經常和幾個同事去朗頓家喝咖啡,這并非趕時髦,當時貴族家庭生活的富裕,在某些方面比內地更加與國外同步。“和其他藏人不太一樣,朗頓家有個客廳門口用英文寫著:請進。客廳里的擺設都是歐式的,家里有專門做西餐的廚師,可以做各種各樣西點。面包每天都烤的,咖啡隨時可以煮。”陳宗烈說,朗頓家不但接受了西式生活方式,思想上也比較現代化,“他的女兒是話劇團的演員,女婿也是話劇團的,漢話講得很好。”帕拉莊園內遺存的為數不多的物件顯示出莊園主人生活同樣豐富多彩。木質的羽毛球拍和琴盒應有盡有,一雙旱冰鞋和記者童年用的幾乎一模一樣;許多講究的帽盒顯示出主人生活的講究。當然最多的還是傳統的奢華品:男主人冬天的臥室里,一圈臥榻上鋪著猴子皮、云豹皮、土豹皮和鹿皮做的坐墊,鍍金的馬鞍并非常人有資格使用,進口的留聲機來自印度。織物有珍貴的金絲錦緞,皮鞋和馬靴則從藏式到英國進口的不下幾十雙。金銀器皿和進口手表根本不能令人驚訝,巨大的野牛角是在藏歷新年里飲酒用的。白多說,這是自己斟酒用的酒具,倒酒時不能發出響聲,否則就罰酒。但是牛角容器的空腔很難不出聲音,不會倒酒的,往往沒喝完就醉了。最令人驚訝的是貴族家的法器。一個上鑲純銀蓋子,下以純金托底的頭蓋骨酒器赫然出現在柜子里。白多說,這必須是高僧的頭蓋骨,用作這樣的法器乃是一種尊重。而另一個據說用處女的大腿骨制作的法號,莊園人解釋,這樣的骨頭來自天葬場,并非取自活人。經濟上的富裕是貴族生活方式的基礎,所有這些財富自然都來自遍布西藏各地的貴族莊園。即便是愛國貴族,在解放后也并沒有馬上擺脫過去的生活方式。第一批入藏的18軍老軍人王貴當時在西藏軍區當作戰參謀,經常和愛國西藏上層人士打交道。那時候阿沛·阿旺晉美已經是西藏軍區副司令,王貴有機會經常和他見面。阿沛在拉薩的宅子里,當時還有十來個仆人,“貴族一般都生活在拉薩,并不住在莊園。只有少數沒有世俗官職的貴族可能住在莊園里。阿沛的宅邸現在拉薩城關區委所在地,但是吃的、用的,一切的東西都由老家工布江達的阿沛莊園運來,到拉薩要七八天時間”。國家對西藏上層愛國人士也非常照顧。陳宗烈說,他們的副主編當時每月工資就有1000多塊,當然發的是袁大頭。“副主編每個月發工資時要叫傭人到機關來幫他扛,否則根本拿不動。”同樣的一幕王貴也親眼所見。阿沛·阿旺晉美當時的工資約為每月800多大洋,王貴等機關參謀每個月的工作之一,就是把阿沛的工資用牲口馱送到他家里去。“他的管家在那里一疊疊地數大洋,夫人則帶著一大串鑰匙在邊上看著。”王貴說,有一次數完之后,馱運大洋的傭人對他大發感慨:“啊呀呀,這么多大洋,怎么用得完啊!”王貴說,阿沛是個聰明豪爽的人,深明大義。后來國家重金贖買他在工布江達的阿沛莊園,大概用了40萬現大洋。但阿沛卻堅決不要,最后用這筆錢為家鄉修了一座橋。王貴說,這樣的事情在貴族中相當少見,并非所有貴族都像阿沛和朗頓等人這樣愛國進步,“貴族壞的我見到的太多了!格布希就是其中一個”。格布希莊園——記憶的沖突巧的是,格布希貴族正是阿沛的姐夫。我問熱心的帕拉莊園導游格桑是否知道格布希莊園,因為這個名字對于在拉薩我問過的所有人都非常陌生。巧的是格桑說他去過:“小時候上學曾經去接受愛國主義教育,不遠,就十幾分鐘。”從帕拉莊園驅車向白朗縣方向,僅5分鐘就到了格布希莊園的土路口。格桑說:“帕拉莊園的(水泥)路是去年新修的,這里就沒人管了。”格布希莊園遺留的唯一建筑是當年莊園的經堂,這是一棟兩層樓土石建筑,墻上刷著貴族才能用的黃色,和村里其他房屋上的白色區別明顯。從建筑格局上,似乎原來應該比帕拉莊園更醒目。兩個高大的舊木質旗桿上掛著新的彩色經幡,經堂前的阿嘎土雖然已經坑洼不平,卻依舊結實,只是門上掛著大鎖。格桑跑了一圈回來說,看經堂的兩個喇嘛去了江孜,不過很快他幫我們找到了藏族老太太彌瑪昌覺,她世居格布希,小時候是莊園的差巴戶,她熱情地請我們去她家在經堂邊的兩層藏式小樓。彌瑪昌覺家二樓經堂柱子上很醒目地掛著兩張裝在相框內并飾以哈達的老照片,一張是一對貴族夫婦,一張是一個年輕貴族。彌瑪昌覺說,這就是當年的格布希老爺。彌瑪昌覺非常健談,格桑說,彌瑪昌覺的兒子是拉薩歌舞團的,在江孜是小有名氣的歌詞作者。彌瑪昌覺跑到另一間屋子給我拿出一本藏文的《多仁家族史》,她說照片和書都是他兒子從內地帶回來的,看得出他們家對多仁家很有好感。彌瑪昌覺家門上銘牌寫著“紫金鄉格西村”。也許正因為音譯的不同,讓許多人感到陌生。據說格布希和多仁是舊西藏人很熟悉的兩個名字,相對而言,多仁是更為常用的名詞,它是該家族在拉薩宅邸的名稱。次仁央宗說,在家族定居拉薩前,多仁家族的名字一直沿用“格西哇”的名稱。但是到了1951年,早已經衰落的該家族實際繼承人已經不是多仁家族純正血統的后裔,而是貴族阿沛家族的一個兒子。次仁央宗說,此人以養子身份成為該家族的實際繼承人。在西藏,貴族血脈的中斷和名號由他人的血脈來延續并非少見,阿沛家便是如此。巧的是,王貴曾經在格布希莊園住過半年,對那里生活的記憶他至今非常清晰。“當時是1952年元月吧,我們駐在格布希,那時封建農奴制度還存在,這是最早的一國兩制了。”住在貴族的莊園照例要付房錢,給的是大洋。王貴說,當時住的是個三層樓的石頭房子,一層是牛羊馬;二層住傭人、管家;老爺在三層。王貴科里的幾十個人就住在二層的幾間大房里。那年藏歷年初一,王貴看到佃戶和農奴約五六十人來到莊園院子鋪的石頭地上。莊園里其他二三百人和王貴的戰友們圍在邊上看熱鬧。格布希老爺則站在三層的窗口。王貴記得這位老爺很瘦,大概50多歲。原來那天是根據去年農奴支差、交租的好壞來做年終賞罰。“去年表現好的坐在前邊的墊子上。墊子厚點兒表示地位高,前邊放個小桌子,桌上有酥油茶。表現差的墊子薄點兒,桌子低點兒,桌上放的是清茶。二三十個人這樣排下去,最后一個就坐在地上了,前邊放一大瓦罐涼水。”王貴說,當時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管家宣布:今天是大年初一,大家來一起喝茶,“只有面前放瓦罐的那個人是被逼著喝的。罐子很臟。我們看到這個農奴一邊哭一邊磕頭、跪下來求也不行。最后幾個狗腿子上來把他按在地上,捏著鼻子將一罐水全部灌下去,灌得那個農奴眼睛直翻白。”“鞭打農奴就看得太多了,捆在柱子上讓管家用皮鞭抽,皮鞭是木頭把的,上面是三根牛皮編成的鞭子。有時候農奴在哭喊,可是管家還在問我們:老百姓不好好地支差該不該打?由于當時的政策,我們既不能干涉也不能表態。”王貴說,格布希虐待農奴是有名的,“我們在他的莊園住了半年,農奴悄悄講:老爺晚上玩兒白天睡覺,最喜歡養小狗。我們見過二三十條小哈巴狗,狗吃的點心是用酥油、白糖、面粉裹起來炸的糖餅,比人吃的好得多。有一次他廚師給他炒菜,里面有個小蟲子,他就叫廚師出去揀一盤子小蟲子,讓廚師全部吃下。晚上玩的勁頭上來了,叫兩個傭人互相打嘴巴子玩,他在一邊看著笑。”王貴1952年8月離開莊園后去了日喀則。他說,格布希莊園后來受阿沛的影響,沒有參加1959年的叛亂,但因為剝削壓迫農奴太嚴重,民主改革時還是被斗爭了。記者在格西村詢問出生在1942年的老太太彌瑪昌覺對50年代的記憶,她興高采烈地說,記得“金珠瑪米”來村里過。“格布希老爺用洋酒和肉歡迎解放軍,我?我跳舞歡迎金珠瑪米。”我聽不懂彌瑪昌覺飛快的藏語,格桑只是斷斷續續在翻譯:“她說格布希老爺對奴隸很好。最后一代莊主很開化。奴隸偷東西,莊主不打不罵,告訴他們下次不要偷了。”彌瑪昌覺說,帕拉莊園的老爺才不好。這真讓人覺得有趣:在帕拉莊園,無論是白多還是格桑,這些農奴的后代都在向我講述最后一代莊園主人的仁慈。比如他給奴隸看病,開辦學校,讓奴隸的孩子可以上學,還包吃包住,遠遠好過格布希老爺。而彌瑪昌覺則對格布希老爺很有好感,她說村民一直希望和阿沛家人聯系,希望他們能籌集些資金修復格布希莊園遺留的經堂。今天的農奴對過去的老爺充滿了懷念和贊美實在出人意料,但無論在帕拉還是格布希,似乎都能發現這種普遍的情緒。帕拉莊園內農奴加工糌粑的廚房土改后曾經住進了以前的農奴。白多說,這些灶臺都沒人拆掉,因為“農奴害怕老爺以后還要回來,所以這些灶臺一直保存到今天”。而彌瑪昌覺解釋為什麼格布希的經堂能經歷“文革”保存到今天,是因為農奴篤信宗教,害怕將來受到懲罰。兩種不同聲音唯一吻合的信息,是格布希太太養的狗。彌瑪昌覺笑瞇瞇地說格布希夫人養了很多的狗,誰都不許碰,她經常帶著它們在莊園里閑逛。說到這里,彌瑪昌覺的笑容燦爛無比。描寫藏族土司生活的小說《塵埃落定》里,小少爺和好幾個丫鬟、侍女發生關系,女奴們似乎都很愛他。記者就此請教陳宗烈,他說:“農奴主和奴隸的關系,講起來內地人都不太相信。我們都是用自己的民族觀念去看世界的,但當時他們那個世界里,卻有自己的一套生活觀念和生活規律。為什麼西藏農奴社會很不好、很腐朽,卻維持了幾千年?原因是農奴主和農奴的關系長期在這種制度磨合下,已經很默契了。當時的西藏就生活在中世紀。”■0閱讀更多更全周刊內容請微信掃描二維碼下載三聯中讀App,注冊就有紅包哦!版權聲明:凡注明“三聯生活周刊”、“愛樂”或“原創”來源之作品(文字、圖片、音頻、視頻),未經三聯生活周刊或愛樂雜志授權,任何媒體和個人不得轉載、鏈接、轉貼或以其它方式使用;已經本刊、本網書面授權的,在使用時必須注明“來源:三聯生活周刊”或“來源:愛樂”。違反上述聲明的,本刊、本網將追究其相關法律責任。
關鍵字標籤:www.eversuntour.com.tw/C/nav/tw/tibet-travel
|